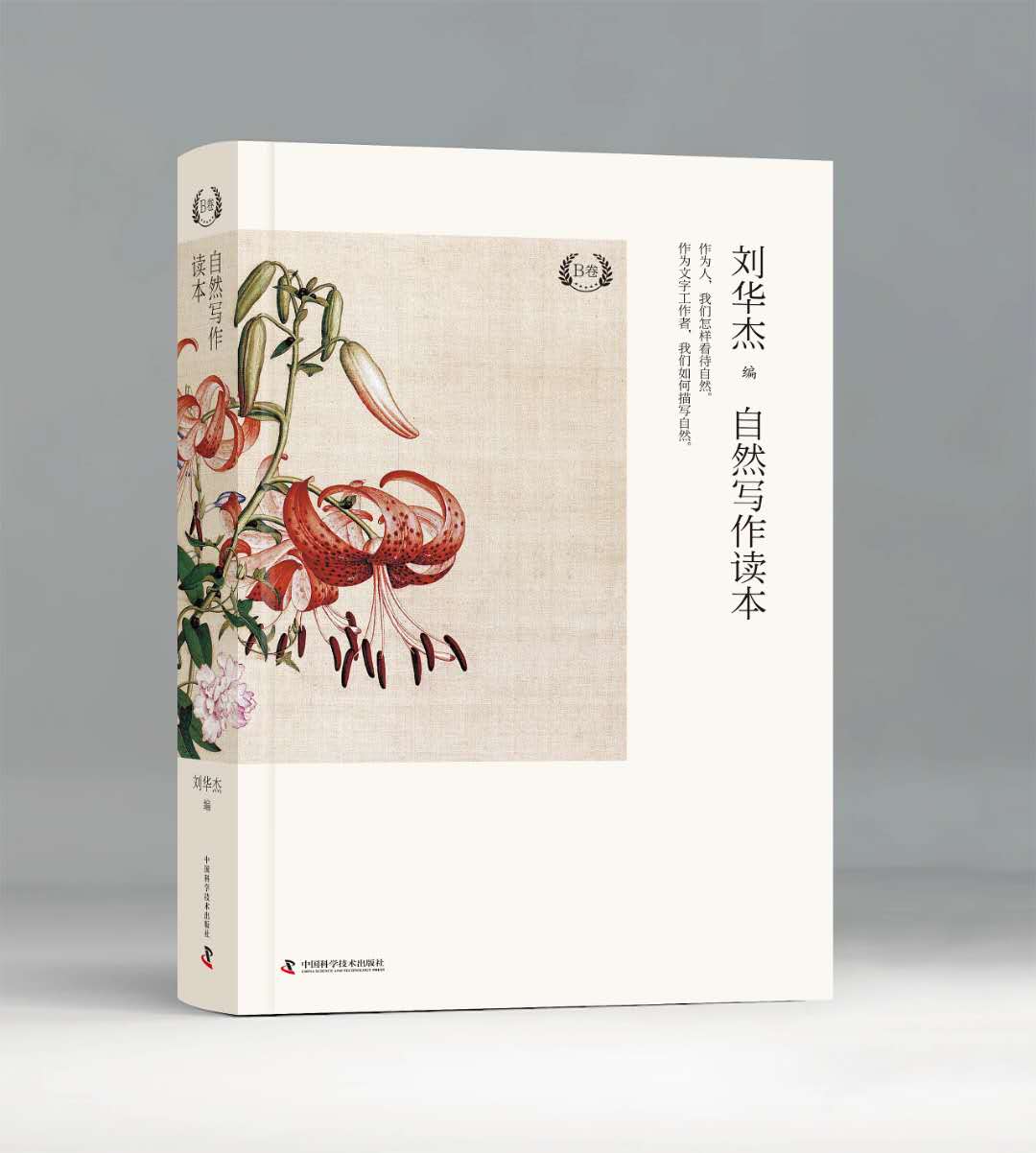
《自然寫作讀本·AB卷》
A卷 阿來編 B卷 劉華杰編
定價:48元(A卷)68元(B卷)
出版社: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

當(dāng)今世界,生態(tài)災(zāi)難和環(huán)境危機(jī)的普遍激化,促使越來越多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到技術(shù)和技術(shù)的發(fā)展問題上。人們提出:是人控制技術(shù),還是技術(shù)控制人?技術(shù)是人的解放者、還是人的奴役者?技術(shù)是“救世主”、還 是“魔鬼”?人是技術(shù)的創(chuàng)造者,還是它的創(chuàng)造物?技術(shù)將把人們引進(jìn)“天堂”,還是將把人們推入“深淵”?……圍繞著這些問題,爭論越來越激烈,參加爭論的人士越來越多,涉及的領(lǐng)域和范圍越來越廣泛。
人們在自然科學(xué)中提出疑問和形成概念是為了建立盡可能精確和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而工程科學(xué)的目標(biāo)則是具體實(shí)現(xiàn)技術(shù)系統(tǒng)和技術(shù)過程。 盡管目標(biāo)不同,但這兩個領(lǐng)域的基礎(chǔ)研究都力圖通過適當(dāng)?shù)膶?shí)驗(yàn)安排,盡可能明晰清楚地研究特定的對象,并用相應(yīng)的數(shù)學(xué)語言加以表述。從邏輯學(xué)的角度看,這兩種研究所用的表述都具有條件命題的特點(diǎn),它們說的是假如遇到一定的原因(前提),物理世界就會出現(xiàn)一定的結(jié)果(結(jié)論)。基于對這種規(guī)律性關(guān)系的認(rèn)識,就可以通過人為的控制和干預(yù),造成一定的原因,從而導(dǎo)致人所期望的結(jié)果。
這種自然關(guān)系可以為任何目的服務(wù)。為獲得科學(xué)和工程知識而設(shè)計(jì)的經(jīng)驗(yàn)的和實(shí)驗(yàn)的方法,是為了精確表達(dá)所研究的過程。然而,這些過程對人們利用它們?nèi)ミ_(dá)到什么目的是沒有選擇性的。它們沒有方向感,只服從自身的規(guī)律,并不排斥人們對它們的任何可能的應(yīng)用方式和應(yīng)用目的。
技術(shù)也是一把雙刃劍,它一刃對著自然,一刃對著人類自己。而人類同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不斷進(jìn)行著能量、物質(zhì)的交換。技術(shù)對自然產(chǎn)生了什么后果,終究還是要反映到人類身上來的,所以,這把雙刃劍對著自然的那一刃,實(shí)際上也是對著人類自己的。
手執(zhí)這把極其鋒利的技術(shù)雙刃劍的人類究竟怎樣運(yùn)用、發(fā)揮手中利器的作用,將取決于他們自己的文化、道德、悟性、價值觀、使命感和責(zé)任感。簡而言之,取決于人的素質(zhì)。這意味著注重成效的“技術(shù)主義”絕對不能取代深思熟慮的“人文主義”。技術(shù)與人文這兩種文化之間的對峙必須消除,二者之間的鴻溝必須填平。它們不應(yīng)當(dāng)相互排斥,而必須是一種互補(bǔ)關(guān)系。
當(dāng)探討技術(shù)發(fā)展的意義和技術(shù)決策的標(biāo)準(zhǔn)時,離不開關(guān)于價值的、倫理的“人文主義”的思索;然而要為解決特定問題技術(shù)上可能的方案確定范圍,并預(yù)測某一些技術(shù)決策的物質(zhì)后果,則必須由科學(xué)家和技術(shù)專家作出回答。
對宇宙和地球的演化來說,億萬年只不過是短促的一瞬間;和悠悠的自然界相比,人類還是一個十分幼小的孩子。玩弄著手中技術(shù)之火的孩子必須格外當(dāng)心,火可以發(fā)光發(fā)熱,但也可以燒上身來。人類在利用技術(shù)之火為自己造福的過程中,切不可隨心所欲,滿不在乎,否則可能身陷火海,化為灰燼。
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賦予人類的巨大力量,要求人類必須具備能與之取得相對平衡的高度自我控制能力。要取得這種力量與控制之間的相對平衡是極不容易的,這或許正是當(dāng)代世界的現(xiàn)實(shí)常常令人進(jìn)退維谷、步履艱 難的原因。要逐步逼近這種相對的平衡,將有賴于人們努力學(xué)習(xí)(特別是創(chuàng)新性學(xué)習(xí)),縮短、消除“人類的差距”,充分開發(fā)尚處于沉睡狀態(tài)的人類潛在的智慧。
本文節(jié)選自《自然寫作讀本 B卷》

阿來,當(dāng)代作家,1959年生于四川省馬爾康縣,藏族,茅盾文學(xué)獎史上年輕獲獎?wù)撸珖舜蟠恚拇ㄊ∽鲄f(xié)主席,兼任中國作協(xié)第八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團(tuán)委員。2018年8月,中篇小說《蘑菇圈》榮獲魯迅文學(xué)獎。
劉華杰,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研究方向?yàn)榭茖W(xué)哲學(xué)、科學(xué)思想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xiàng)目首席專家,博物學(xué)文化倡導(dǎo)者,植物愛好者。主要作品有《渾沌語義與哲學(xué)》《分形藝術(shù)》《檀島花事》《博物學(xué)文化與編史》《博物人生》《從博物的觀點(diǎn)看》《崇禮野花》《中央之帝為渾沌》等。作品曾獲得文津圖書獎、十大自然好書獎、大眾喜愛的50種圖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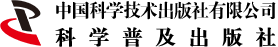

 微博
微博